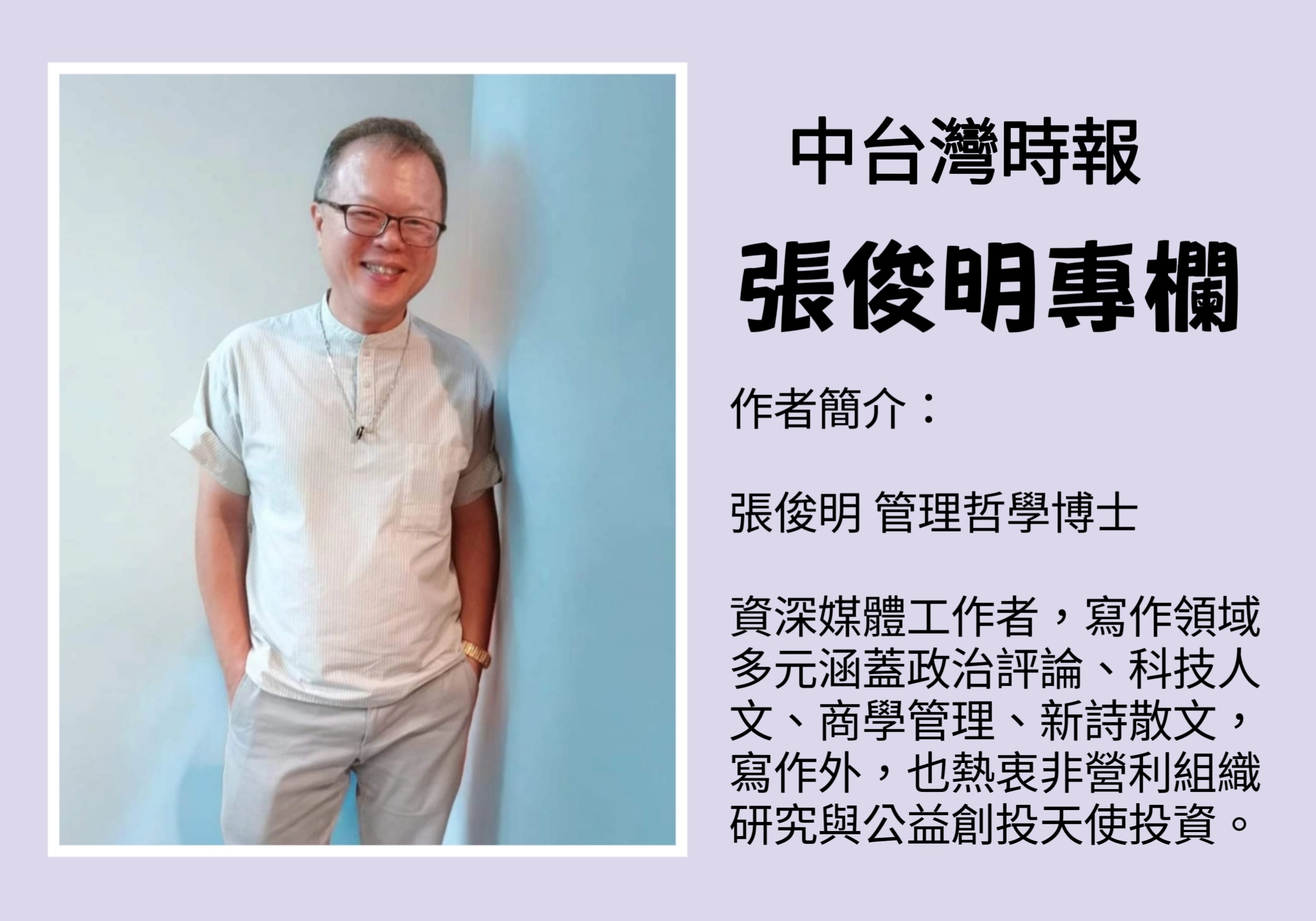美國在二戰後主導建立布列敦森林體系,其核心在於以美元作為全球貨幣體系的支柱,所有貨幣與美元掛鉤,而美元則承諾與黃金兌換,這不僅為戰後重建提供穩定,也讓美國藉由貨幣與金融主導權坐上全球霸主寶座,這種「金本位」制度設計看似建構於合作與共識,實則是一種制度化的美國中心主義。當美國發現「金本位」不再有利自身時,1971年尼克森總統宣布中止美元兌換黃金機制,即所謂「尼克森震撼」,一夕間拆解了整套體系,顯示美國對於全球規則的承諾,只建立在「符合美國利益」的基礎上。
如今川普正在做的事情,本質上與當年布列敦森林的「建立與喊停」有著驚人的對照。只是這一次,他不是打造一個體系,而是主動拆除既有的全球化秩序。川普執政期間強調「美國優先」,對國際協定、貿易規則、盟邦承諾屢屢翻臉,如退出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》(CPTPP)、巴黎氣候協定、世衛組織(WHO)等。他的國際政策不僅反對中國崛起,更精準而言,是反對「任何不再讓美國繼續主導的全球化」。從布列敦森林到WTO世界貿易組織,美國在全球經貿體系中的角色始終是既得利益者。根據《外交事務》(Foreign Affairs)期刊的研究指出,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掌握金融、科技與資本流通三大核心優勢,使其在冷戰後成為最大的贏家。然而,2008年金融危機後,美國經濟疲弱、製造業空洞化、社會貧富差距擴大,再加上中國以「中國製造2025」與「一帶一路」戰略逐步挑戰全球供應鏈主導權,美國開始感受到「自己打造的全球化」竟然逐漸不利自身。
川普的對中貿易戰不是起於意識形態,而是來自對經濟秩序主導權的焦慮。2018年起針對中國課徵懲罰性關稅、限制科技輸出、圍堵華為、施壓盟邦「去中化」,其背後邏輯是「中止讓對手從全球化中壯大自身的機會」。對川普而言,這不是反中,而是反「全球化已成美國負資產」的現狀。他甚至主張對美國企業在中國設廠課重稅,目的就是把全球化的利潤鏈條「拉回美國」。川普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,而是那個認為「遊戲規則不再讓我贏」的玩家。他的行動仿佛是對布列敦森林時代的回音:當規則對我有利時,我制定它;當規則讓我吃虧時,我就撕毀它。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瓦解標誌著金本位的終結;而川普的外交政策,則可能標誌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終結。
值得注意的是,這並非單一政治人物的偏執,而是一種「美國重新計算自身在世界中的價值交換」的體現。川普的做法雖被稱為民粹、保護主義,卻深獲基層與工業州選民支持。這些選民並不反對全球接軌,而是反對那種「全球繁榮,美國製造業凋敝」的交換邏輯。正如美國學者Samuel Huntington在《我們是誰?》中指出:「當國家精英與全球利益掛鉤時,國家認同的危機就會浮現。」川普也並非完全否定國際合作,他主張的是一種單邊主義式的「可控全球化」。例如,他希望北約為軍費支出買單、強迫盟友簽訂有利於美國的貿易協定、對他國貨幣政策施壓以維持美元優勢。這是一種扭曲的布列敦森林再版,只不過不是建立體系,而是「美國主導、其他服從」的全球交易結構。
也許,川普不只是反中或反共,他挑戰的是過去30年由美國主導卻演變為「利潤全球化、責任本土化」的體制。在他眼中,全球化不再是美國的工具,而成了他國壯大的平台,與其等待下一場「和平演變」,不如主動「切斷互惠」,回到強權主導的競爭格局。我們正在見證的是一場制度性裂解,當年美國透過建立體系收割紅利,如今透過解構體系防止衰退,川普的全球戰略,其實就是告訴世界「當全球化不再是我的武器,它就不值得存在」,如此操作,表面是美國自保,實則也逼迫世界重思,在美國缺席或翻臉的未來,誰還能主導一場新的布列敦森林?這也許就是川普版的「尼克森震撼」!只是這一次,美國震撼的不只是金本位,而是整個後冷戰的全球秩序。